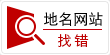人们对目前地名学的状况不甚满意,深感拘守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其历史局限性,这是造成地名学进展缓慢,甚至引起自身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地名学要有所突破、有所发展,它自身首要的内在条件正在于方法论的革新。而方法的更新又应以是否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为评价标准,应以研究观念的更新为前提。
(1)将某一民族语言地名的中心词(通常是地名通名)跟亲属语言或方言有关的词比较,从现代语言的形式,意义方面追溯到古代语言。
(2)在某一语言范围内确定构成地名其它成份的词义,对地名作合理的解释。
例如金祖孟先生在《地名通论》(《新中华》〔复刊〕1945,4)一文中对中西地名的差异作了比较研究,列举了五个方面的不同:第一,中文重字形,而西文重读音。因此,中文地名的变化由人为更换,而西文地名的演变系自身变化。长沙一名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,因为未加更换,所以始终不变;马德里(Madrld)本作Magerit,虽未加更换,亦变化而成今日拼法。第二,中文稳定,而西文易变。所以,中国的上古地名,大多尚能望文生义,而西方的中古地名,十之九已不辨来源。“长沙”两字同新地名一样的意义明显,而柏林、维也纳的文字与意义,迄今尚异说纷纭。第三,中文地名的结构复杂,而西文地名大多结构简单。“衡阳县”“泰安县”一类地名,在西文可说完全没有。第四,中文地名常能与较少的字数表示丰富的含义。如“衡阳”,虽仅二字,却能表示明确位置。“泰安”,虽仅两字,而客观事实与主观意志兼而有之。此类地名为西文所少有。第五,同一地名,其西文字母数常较中文字为多,西文地名较中文地名为长。在地图上注记地名时,中文地名宜于注点(城镇),而西文地名宜于注线(山河);中文地名易于小区域,而西文地名宜于大区域。

区域比较方法还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比较。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。